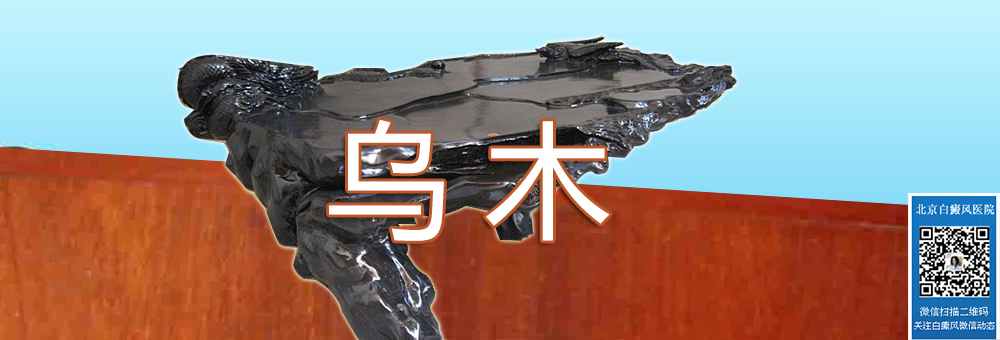
南方的春天,是吹面不寒杨柳风,沾衣欲湿杏花雨。北方的春天,是杨絮柳絮钻鼻孔,大风起兮沙飞扬。没去过北方,南方人想象不出什么叫素衣莫起风尘叹。没去过南方,北方人想象不出什么叫小楼一夜听春雨。没去过京都,熟读唐诗的中国人也想象不出什么叫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。预警:以下文字全是我,一个南方人的个人偏见。过去几年的春天,两年在北京,两年在京都,今年才回到熟悉又久别了的广州。众所周知,广州是个「四季乱序播放」的城市,季节感不似北京和京都那么强。但广州还是有春天的。「广州的树是春天换叶子的,一场春雨,一夜之间旧的叶子掉光,又一夜之间长出新芽。」我曾经跟好些北方朋友这般描述广州的春天,对方总觉得无法想象。在他们的认知体系里,树木都是秋天落叶,冬天光秃秃,春天长新叶。广州的春天固然有很多美丽的花,红花羊蹄甲(紫荆花),大叶紫薇等等,还有师奶捡来煲粥的木棉花,但在我心目中,大叶榕换叶子才是广州春天的象征。每年一到大叶榕换叶的时候,我就想回母校中山大学看看康乐路的「大叶榕隧道」。风起时,站在树下,细嫩的叶芽漫天飘落,比花瓣雨还美,给我对生命和季节的感动不亚于樱吹雪。随后,新叶很快舒展长大,密密遮住天空,即使四季常绿,也是这个时候的绿最鲜嫩可爱。中大别名「康乐园」,是康乐公谢灵运被贬到岭南时的居所。不是很多人知道,这位大诗人是在广州被皇帝下诏就地处死的。谢灵运的本家前辈诗人谢安,曾经在赏雪时给侄子侄女出题「白雪纷纷何所似?」侄子谢郎答「撒盐空中差可拟」,而侄女谢道韫答「未若柳絮因风起」,显然比哥哥的才情高出许多。柳絮也是春天的标志。「试问闲愁都几许﹖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*时雨。」贺铸的词从小背熟,但柳絮到底是什么?我不知道。广东只有「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」,只有青青柳枝,清明时摘几枝插在门口。柳树和杨树在我心目中都是很诗意的树,「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」,杨过姓杨,小龙女因而化名姓柳。直到那年北漂帝都工作,正好在春天搬过去,我才 次见识到柳絮。确切说,我其实不知道那是柳絮还是杨絮,只看到地上一团团的,就……挺脏的……真的跟诗意没有半毛钱关系……那时候还不知道戴口罩,总是觉得鼻子痒痒的,不是必要的话就别张嘴,不然让你一秒学会B-Box。后来北京兴起潮汕牛肉火锅,老板知道我是广东人,特意请我吃潮汕火锅解乡愁。小馆子在路边敞开门,我倒是不介意这种馆子,只是看见有柳絮还是杨絮飘了进来,轻盈又准确地落在肉上牢牢粘住,老板手起肉落锅,那朵絮儿就此消失在翻滚的肉汤中。我好像觉得喉咙也痒了起来,牛肉也不香了……我可真是个矫情的广东人!柳絮那么会飞是因为它比鹅毛还轻得多。你知道吗,帝都一年会产生吨柳絮,相当于2万头猪的重量!早上起床,我习惯性地打开窗通风透气,这是多年老妈教诲的结果。后来我才懂得必须关上纱窗,不然柳絮会飞到满屋子都是。后来我又才懂得连窗也不能开,不然沙子会进来……曾经住过朋友的四合院,晚上在院子里看电影蛮舒服的,但要是拿出电脑打字,指尖就会触到细尘,擦也擦不干净。而在广州,我家阳台门一直敞开,此刻我吹着凉风写这篇文章,键盘的手感依然清爽。北京的风很大。有一部拍得很粗糙的纪录短片《北京的风很大》,算是国产独立纪录片鼻祖之一吧,导演扛着摄像机逮到人就问「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?」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在茅坑里问,被在蹲大坑的人一顿骂。看这部片子时我还没去过北京,南方的春风是「吹面不寒杨柳风」。后来终于见识到北京的大风,啊,原来春天也能刮大风,那风好像能带走我身上所有的水分,喝多少水都不解渴。曾经做饭剩下半只茄子在砧板上没收进冰箱,第二天惊讶地发现它干瘪了。买了一台小加湿器给桌面的蕨类植物喷水雾,它们还是越来越蔫。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植物,行尸走肉。而在广东只会担心潮湿发霉,墙壁会流泪。从书架抽出一本书,发现书肚子竟然长了点毛,再一看,天哪,书架内壁一层毛!这是在讽刺我不看书么,赶紧把书都搬出来晒!说相对湿度的话,北京是18%,广州可以去到81%。广州的春天多雨,大雨能下几天,小雨是「沾衣欲湿杏花雨」。金戈铁马的爱国诗人陆游,也会写些很细腻温柔的诗句,我特别喜欢「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」。古龙的小说《圆月弯刀》里,有一把弯刀上刻着「小楼一夜听春雨」,我总觉得那一夜发生了点故事,多半跟情有关。「矮纸斜行闲作草,晴窗细乳戏分茶」也是风雅又工整的对仗。而诗里的另外两句「世味年来薄似纱,谁令骑马客京华」,「素衣莫起风尘叹,犹及清明可到家」,年纪大些才懂个中滋味。那些文人呀,总是成天嚷嚷着要回老家去。但陆游家乡在绍兴,离这首诗的写作地点临安(杭州)也没多远。更刚的是西晋张翰,在洛阳为官,思念家乡苏州的菰菜(茭白)、莼羹和鲈鱼脍,毅然辞官归故里:「秋风起兮木叶飞,吴江水兮鲈正肥。三千里兮家未归,恨难禁兮仰天悲。」洛阳的秋风应该比江南要猛,树叶乱飞。客京华的我,思念着广州的虾饺肠粉,糖水,蚝油菜心,清蒸鲈鱼,西洋菜汤……从冬天想到春天,到春天的沙尘暴。北京的沙尘暴,我见识过两次。 次,躲在家里关紧门窗不敢出门,看到白天变成了*昏,世界变成了锈红色。第二次,已经对北京有了去意时,得到一个颇让我心动的工作机会,我十分纠结,要不要为此在帝都再熬一年?当晚刮起沙尘暴,第二天出门,路上倒了许多大树,车都叫不到,只能提心吊胆地骑车去上班。我告诉自己那是天意。素衣莫起风尘叹,犹及清明可到家。我固然喜欢北方的四季分明,喜欢看红叶冬雪,我也不喜欢广州春夏的潮热,但从北京回到广州,呼吸到湿润的空气,绷紧的皮肤放松了,喉咙不再觉得渴,我才会感到,身体和心的一部分苏醒复活了。从北京到京都, 被治愈的依然是呼吸。 次去京都时是四月下旬,樱花季已过。爱上京都的起点,是岚山深处的一座小寺庙祇王寺,当时尚无名气,这几年来已经芳名在外。还有雨中的龙安寺和南禅寺。体会京都的美,不必非得赶樱花季。樱花虽美但易逝,花期飘忽让很多人扑空失望,有名的花见点都人满为患,而且樱花开的时候还有点冷,风也吹得脸干干的。樱花季过后的春末则是京都比较安静的时节,可以自己坐着看一天,无人打扰。春末雨水多,蓬勃生长的青苔和青枫看在眼里,就像滴了眼药水一般清心润肺。尤其当你带着北京的风尘来,那种体会更是加倍强烈。青苔对空气湿度和质量极为敏感挑剔,在帝都怕是养不了。京都有个私家园林,主人闭园养了几十年的苔和枫,最近才限定开放。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都问过我同一个问题:你为什么喜欢京都?因为啊,「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」「竹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」,这些我小时候熟读却想象不出来的诗句,在京都都是眼前实景;「曲水流觞」这种在中国已经失传的风雅事,被京都人变成用竹筒吃流水素面消暑;京都人春天吃樱花和果子,夏天吃夏柑糖,秋天吃栗子,吃穿用全是「季节限定」,过得跟我们古代诗画里的一样。我们祖上曾经富过,后来家道中落,本事都给邻居家的孩子学去了,代代传下来,我们去到邻居家做客,才相信原来那些美好真的存在过,而且还能在现代社会延续。这种赞叹中带着不甘的复杂心情,怕是外国友人不容易体会,中国人更懂得。喜欢京都的根本原因,是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深爱,这种心情你也懂得吗?扯远了。如果既喜欢四季分明,又受不了北方的风沙严酷,那京都就是 选择了。只可惜京都是盘地,夏天闷热更胜广州,冬天阴冷却少雪。而且,京都虽好,终是他乡,还是带着距离看最美。海棠无香,鲥鱼多刺,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只能选择最让自己舒服自在的地方栖居。当然了,今年错过了京都的樱花季,还是有点可惜。我们都错过了今年的春天,当再次见到的时候,我一定会加倍珍惜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-END-撰文、摄影/骆仪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如果你五一也不出门,就看看我推荐的旅行书单吧为什么这些旅行好书登不上畅销榜?关于日本我还写过日本不是我的 ,因为…太完美了中国人找了千百年的桃花源,贝聿铭在日本造了一个或